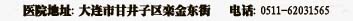痛风,是日常生活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年中国痛风诊疗指南》指出,我国痛风患病率为1%~3%,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阔的疆域,估计我国痛风患者至少在1千万以上,并呈现不同的地域性特点,沿海区域患病率更高一些。
近年来国家对痛风的诊疗非常重视,发布的相关指南包括《中国痛风诊疗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膳食指导》、《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等,同时在基层加大了有关宣传和介绍,使得痛风患者可以得到更加及时、有效的治疗。可是临床实践发现在痛风治疗的规范性上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国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CRDC)的数据显示,痛风患者3个月的血尿酸水平达标率只有29.12%,6个月达标率也仅有38.2%,急性发作后1个月的随访率仅为20%左右[1]。这些数据均提示治疗痛风,必须从规范性做起,而以下五个步骤或能相助一臂之力。
(一)准确诊断是前提
年ACR指南的痛风诊断标准为:关节液中有特异性尿酸盐结晶,或用化学方法或偏振光显微镜证实痛风石中含尿酸盐结晶,或具备以下12项标准(临床、实验室、X线表现)中6项或以上:
1)急性关节炎发作>1次;
2)炎症反应在1天内达高峰;
3)单关节炎发作;
4)可见关节发红;
5)第一跖趾关节疼痛或肿胀;
6)单侧第一跖趾关节受累;
7)单侧跗骨关节受累;
8)可疑痛风石;
9)高尿酸血症;
10)不对称关节内肿胀(X线证实);
11)无骨侵蚀的骨皮质下囊肿(X线证实);
12)关节炎发作时关节液微生物培养阴性。
对于临床来说,这些标准已经非常有用,但鉴于偏振光显微镜及培养等检查没有普遍开展,很多人容易简化成“第一跖趾关节疼痛+血尿酸升高=痛风”的公式,造成了痛风的过度诊断,也常常忽略了其他可能性,如“蜂窝织炎、丹毒、感染化脓性关节炎、反应性关节炎、假性痛风”等。
因此在我国年及年ACR/EULAR的新指南里都在临床指征上加入了影像学检查,如超声和能谱CT(见下图)[2]。这些指标的纳入使得痛风诊断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值得一线医生在临床实践中采用。
(二)找准根源是关键
众所周知,高尿酸血症与痛风密切相关,建立在嘌呤代谢异常基础上的机制导致了炎症的发生,下图对痛风的病理生理学的发病机制进行了一个概括[3]。
基因、环境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国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呈逐年上涨的趋势。一项关于-年武汉地区高尿酸血症的研究[4]显示,各年龄段尤其是男性在这十年间在不断上升,这可以解释近年来痛风患者不断增多的现象。重视对高尿酸血症机制的研究对未来的痛风治疗有着重要意义。
(三)完整评估是标尺
对痛风的完整评估一直容易被忽略,仅仅注重关节和痛风性肾病的评估不足以全面了解痛风患者的全貌。鉴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传统高危因素与高尿酸血症的紧密联系,在患者就诊时完善相关疾病的病史和用药情况尤为重要,如使用利尿剂降压可能导致尿酸的波动。已经有心血管高危风险的患者注意通过结合心脏、血管彩超等指标综合评估患者的整体状况,从而为下一步的药物治疗提供更加安全有力的凭据。
(四)合适药物是重点
随着痛风诊疗指南的不断推进,“控制急性期炎症+降尿酸”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武林秘籍”,“秋水仙碱/非甾体药物/糖皮质激素”等三大常规控制急性期药物以及“别嘌醇/苯溴马隆/非布司他”三大降尿酸药物成为了医生手中有效对抗不同时期痛风的“三板斧”,但日常使用中需要细心组合才能兼顾疗效和安全性。
例如,指南里推荐采用COX-2抑制剂能更有效减少胃肠道损伤等副作用,可以用于有消化道高危因素的患者,这就是考虑到痛风患者常存在长期不规律使用镇痛药物或饮食不节律等实际情况。再如已有肾脏损害或高危心血管风险的患者,非甾体药物的运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风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降尿酸药物中。下面两张图汇总了痛风治疗药物对于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涉及的药物种类仍然局限,但可以提示我们,